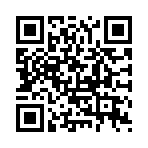超常教育合理嗎?中科大少年班畢業生活躍在商界
原標題:超常教育合理嗎?中科大少年班畢業生不少活躍在商界

前不久,13歲女孩陳舒音考上浙江大學的新聞,讓超常教育的爭議再起。
9月1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發布2018年少年班招生辦法,面向全國招收200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優秀高二(含)以下學生。
而在今年的招生中,有兩名浙江籍新生,王哲和張浩然。
中科大的少年班肇始于1978年,到今年已是第四十一期。
中科大對少年班歷來低調,而這也使得少年班在外人眼中愈顯神秘。
錢報記者走近中科大少年班的兩位浙江學子,回溯他們的學習經歷,還原爭議背后真實的求學路。
未成年的他們是否能夠適應大學生活?旁人口中的“天才”,在同學、師長、父母眼中又是怎樣的少年?
家長:真的是湊巧了
兒子考進了少年班,王哲的父親卻顯得有些不好意思,連連說:“湊巧,真的是湊巧。”
他說“湊巧”,是因為兒子提前一年上幼兒園,年齡剛好符合少年班的錄取門檻。
此后王哲的求學路幾乎是按部就班,既沒有跳級,也沒有展露特別的天分。“他從小學到初中,別的家長都要求小孩考100分,我覺得差不多就行了。”王爸爸說他對兒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快樂成長,享受童年”,所以上補習班這樣的安排從未出現在王哲的學習里。為此,王哲還曾經吐槽過父親的“放養政策”。
那年王哲剛轉入溫州育英國際實驗學校小學部,第一次數學考試,王哲破天荒地考了70分。“回家后眼淚汪汪,說他這輩子都沒考過這么低的分數。”即使升入初中,王哲的成績大多數時候徘徊在班級20名上下,王爸爸笑說,“他還埋怨過我,說‘爸,你不給我報補習班是不是為了省錢’。”
父母從未想過王哲會考上中科大少年班,事實上,直到高二開學前,王爸爸對中科大少年班的認識幾乎是零。甚至報名后,王爸爸也未將這事放在心上。不止王爸爸,當時正忙于物理競賽的王哲對此也沒有很上心。直到高考前一周,當王爸爸問起兒子的復習情況時,正在長沙備賽的王哲答復還是“書都沒帶,不復習了”。
未曾想,就是這么一個6月3日才開始準備高考的學生,最終殺入了全浙江僅有2人入圍的中科大少年班復試。
“你們跟黃老師談談吧。”王爸爸建議錢江晚報記者去見見王哲的班主任黃強,“黃老師對他的影響很大。”
班主任:我見過太多天才,他不算是
溫州育英國際實驗學校的宣傳欄里張貼著“2017年高考金榜”,高二八班有三名學生提前上榜,王哲在中科大少年班,胡杰和羅晨在中科大創新班。
“一眼看過去氣色最好的三個就是他們。”班主任黃強開玩笑說,有沒有經歷高三一年的“折磨”,“看臉就知道了。”
“當時奧賽剛結束,準備了一年卻鎩羽而歸,學考時間又緊迫,兵臨城下。”黃強回憶說,他帶的是競賽班,“我們準備了很久卻抱憾而歸,學生的情緒難免沮喪。”
中科大少年班就在那樣的情況下被黃強推薦給他的學生們。“少年班的錄取條件很嚴苛,我鼓勵王哲他們,既然年齡符合,為什么不去試試?考上了,去不去到時再說嘛。給自己多一個選擇有什么不好呢?”最終班里有14名同學報名中科大少年班招生,經過兩輪考試后,有三人被錄取,其中兩人去了創新班。
從初中時的班級前20,到高二考上中科大少年班,王哲算是“天才”學生嗎?
“我見過太多天才,他不算是。”到溫州育英任教前,黃強是河北衡水中學教師,全國知名中學,長期包攬河北省文理科高考前十的學校,他有底氣說“見過太多天才”。在他看來,天才往往無師自通、舉一反三,大多數學生都不是“天才”,但這并不重要,“少年班是條‘蹊徑’,并非是‘天才之路’,至少我是這么看的。”事實上,黃強認為少年班恰巧適合不那么天才的學生,“現在和當年不一樣,天才學生有太多選擇,反而是那些‘陪跑’生,如果剛好他又足夠努力、自律且有自我想法,不如去試試少年班。”他欣賞王哲,喜歡胡杰和羅晨,不是因為所謂“天才”,反而是因為他們都有一顆平常心,“心態特別好。”
與王哲的情況相似,在蘭溪一中,張浩然的成績也不是最好的。“但他心理素質好,不關注每次考試‘一城一地的得失’。”張浩然在蘭溪一中的班主任李洪增如此評價學生,“學習累了,他會給自己減壓,出去打打羽毛球、看看美劇,即使到最后的沖刺階段,每次周末回家,都要看美劇。”
張浩然不僅考取了中科大創新班,隨后又以浙江省“狀元”的成績,收到了中科大少年班的錄取通知書。兩份入學書接踵而至,張浩然沒有放飛自我,而是繼續上課,還參加了學校的期末考試。“這是我在蘭溪一中的最后一個學期,我要完成這最后一步。”
李老師笑言張浩然是“辦公室常客”,有時候上完課回去,老遠就能看到等候多時的張浩然。“他問題意識很強,常常就一道題,能引申出好幾個問題。”在李老師看來,張浩然最大的長處是自覺。考上少年班之后,還沒正式報到,“他已經開始儲備大學英語詞匯了。”
自己:提前一年入學,沒什么不好
“他(王哲)走之前跟我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哥先走了,你們繼續加油’!”王哲的高中同學徐良澤說起這件事就想笑,因為這位“哥”實際上剛滿15周歲,比同班同學都小。
“我可沒這么說啊。”中科大少年班新生正式開學前的最后一個周末,錢江晚報記者見到了王哲,剛剛結束軍訓的他比兩個月前登上“金榜”時略黑了一些,并沒有想象中的稚氣,說起高中同學之間的玩笑話,他說話不緊不慢。
若按部就班,這個時候他應該跟同班同學一起念高三,如今卻比大多數同學早一年開始大學生活。談到這樣的變化,王哲很平靜:“從小學就開始住校,習慣了,沒什么特別。”他一邊說,一邊領著記者去他剛在自習的新圖書館轉轉。課程還沒開始,他已經基本適應了大學的學習節奏。“要說不同,大概就是現在的住宿條件還不如以前吧。”宿舍沒獨立衛浴,也沒WiFi,這跟王哲想象中有些不一樣。“但這不重要,反正可以來圖書館。”
他開始融入校園社交生活,想要加入學校的動漫社。“不過我太小白了,他們討論的都很專業。”這個旁人眼中的“學霸”,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動漫粉”。
話題轉到了王哲的求學選擇上。“少年班并不是我的第一選擇,相比之下更想去北大。”王哲回答得毫不猶豫,最終選擇了少年班,在他看來,一是少年班大一不分科,有選擇余地;最重要的一點,是可以提前一年入學。
時間,對他來說無疑是重要的。在談話時,王哲最常做的動作,就是微微抬起手腕看手表。他從高中就一直保持的作息時間:每天早上6點20分起床,晚上10點半睡覺,午休半小時。至今不變。跟記者聊完,他轉身回了圖書館,繼續被打斷的自習。
張浩然跟王哲成了室友,兩個人都喜歡物理專業。在他們宿舍樓下,玻璃大門的門楣上貼著六個大字:少年強,中國強。
直到高考前一周,當王爸爸問起兒子的復習情況時,正在長沙備賽的王哲答復還是“書都沒帶,不復習了”。
中科大少年班的宿舍。
少年班,是不是一個“最優”選擇
雖然考上了,但直到去中科大少年班報到前,對于王哲的未來,他的父母仍有分歧。
在媽媽的設想里,她更希望兒子能如常參加高考,去北大、清華;而爸爸在經歷了少年班的嚴苛選拔之后,覺得機會來之不易,不該放棄。
中科大少年班最初的“光環”,來自寧鉑、謝彥波、干政等一批少年大學生,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神童熱。
受熱潮影響,繼中科大之后,全國有12所大學先后辦起了少年班,在招生過程中逐漸陷入了低齡化、偏科化的誤區。
上世紀90年代以后,受困于教學成本、生源質量、學生心理素質等原因,各校又紛紛停辦少年班。也由此引發了對“超常教育”的持久爭議。
如今,全國僅剩中科大、西安交大與東南大學仍開設有少年班。
少年班到底是不是一個“最優”選擇?到底有沒有價值?經歷過的人應該最有話語權。
改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初衷調整
在中科大少年班學院一樓門廳,懸掛著少年班往期校友合影,從每期的合影人數,大致能看出少年班學生規模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經歷過一波增長,而后趨于穩定。
“那時候中科大少年班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神’一樣的標識,能考上確實是非常(值得)驕傲。”閔萬里,阿里云人工智能首席科學家,中科大少年班1992級學生,入學那年14歲。“高一的時候參加了數學競賽,得獎后在寒假去中科大參加集訓,被老師蘇淳教授推薦報考少年班。我們班上還有13歲入學的同學,大家(年齡)都在13~15歲。”
與現在不同,當時中科大少年班是五年學制。“少年班的教學方式是狠抓數理基礎,不指定專業,到了大三下學期請學生自己選專業。”閔萬里說,他至今仍特別感恩當年打下的數理基礎。
畢業20年,每次提到他的教育履歷,中科大少年班總是很“搶戲”,盡管此后閔萬里去了常年位列各種大學排行榜世界前十的芝加哥大學繼續深造,但在外人看來,都不如“少年班”的求學經歷更能證明他的“天才”。
閔萬里并不認為自己“天才”,或許少年班的學生里有“天才”,但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天才”是一種過譽的形容,甚至是對他們努力的否定。
在他看來,少年班最寶貴的是在超常教育領域實踐積累了很多有益經驗,知道如何對學生個性化因勢利導,并鼓勵批判性思考。這些讓他至今受益。
少年班學院院長陳旸在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及,中科大少年班能維持至今,經歷了相當多的轉變。“如果說少年班成立初期,我們的初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話,那么如今,我們更希望探索一條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模式。”
妥協:不再過分限制年齡的創新班出現
2010年以后,在少年班30余年辦學經驗的基礎上,中科大在秉持以往特色招生選拔模式的同時,逐漸放寬了年齡限制,在“少年班”之外又開辦了“創新試點班”。今年即將讀大三的王昌煜是創新班學生,他告訴錢江晚報記者,學院針對創新班與少年班的學生,開設的課程、授課老師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說,除了年齡外,學校在教學資源上對兩個班的學生是“一視同仁”的。
王哲高中班主任黃強說,當初他聽到這個消息,就有了一些推測。“現在的學校,往往更樂意把尖子生送去清、北,而中科大新推出的創新班則是與少年班同時在高二招生。”這種做法,一是為了避開清、北的“圍剿”,二是把提前入學作為它的最大賣點。但在黃強眼中,這多半也是出于生源考慮的無奈之舉。
占到整個少年班學院人數四分之三強的創新班,不再將年齡作為限制,從中也可以看到中科大少年班在教學理念上的轉變。
選擇:少年班畢業生不少活躍在商界
中科大少年班學院大四畢業生陳楚白,即將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化學專業碩博連讀,對于自己的求學之路,他說是“意料之外”:最初沒想過要上中科大,去了少年班學院他沒想過要出國。
“大二以后,很快進入了實驗室,開始專攻科研。”陳爸爸說,少年班學院的老師很嚴格,所以也有學生會掛科。事實上,每年都會有少年班學院的學生因為課業等原因選擇退學。“少年班里確實有一些理解力超群的天才,但大部分人依靠的還是后天的努力。像楚白在科大,從周一到周日,每天都要忙到晚上十一二點才睡,四年下來,連近在咫尺的黃山都沒去過。”
“其實我和他媽媽比較現實,當時想讓他選金融、管理或是中科大的3+2項目,在國外讀個碩回來,好找工作。我們覺得做科研又辛苦又清貧,但楚白說談錢太俗,他想做學術。”陳楚白同時收到了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學等三所大學的錄取通知,學費全免,每年還有3萬多美元生活費。最后選了伯克利分校,8月初已去就讀。
看起來,陳楚白走的每一步都有偶然的成分,但歸納起來,他的求學路徑在中科大少年班學院里非常典型:奧賽出成績——被少年班學院錄取——專攻科研——出國深造。
陳爸爸說,楚白的同班同學里,三分之一以上選擇了出國求學,還有三分之一選擇保研去了國內各大知名高校與研究所,高達80%的學生選擇了繼續深造,直接就業的屬于少數。
中科大去年曾做過統計,過去38年里中科大少年班共畢業超過3400名本科生,約90%考取國內外研究生。畢業十年后的學生中,有超過200人成為國內外名校和科研機構教授;另有55%投身于企業界、19%活躍于金融界,在世界500強任職者達到35%。
用陳楚白的話來說:“大學為我們提供了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你的能力,決定你有多少種選擇。”
這苗,到底拔不拔
跟浙大文科資深教授史晉川說起“少年班”的話題,他忽然問我:你怎么看超常教育?
這位77級大學生的同學里,也有幾位“天才少年”,比如他的同班同學、現任浙大副校長羅衛東,上大學時也未滿15周歲。
“‘少年班’是選拔能力超常學生的一種方式,這我是贊同的,但要不要獨立成班?我認為值得商榷。”史晉川說,以他親身經歷來看,真沒有獨立成班的必要,“77級大學生的生源算是歷屆里包容性最大的了吧,年齡跨度相差十幾歲,一樣相處融洽。那時候請衛東幫我們傳情書,摸摸腦袋,他開開心心就去了,現在想起來都還是很美好的回憶。”
如果需要特殊照顧、資源傾斜才能培養出人才,教育失之公平,又怎么證明這些學生具有“超常能力”?
包括中科大少年班在內,國內對能力超常學生的培養基本是依靠“加速”來完成。
這至少說明,12年制傳統教育是有很大彈性空間的,未必適合每個學生。
超常教育有沒有問題?有。但問題不在于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而在于它還不夠完善,比如有不少評論認為少年班是“拔苗”班,未必有利于孩子成長。
史教授最后說,人生漫長,何處不可學,順其自然吧。
用陳楚白的話來說:“大學為我們提供了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你的能力,決定你有多少種選擇。”
[編輯:可可]- 相關閱讀 更多 >>
-
- 大學畢業生創業調查:近四成創業者為農村家庭背景 2017/09/15
- 人社部實施三支一扶計劃 畢業生享就業創業好政策 2017/09/14
- 西安交大少年班青島招生:15歲以下應屆初中生 2015/11/26
大家愛看